|
元代水军训练及军事科技教育
王风雷
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
蒙古人以武定天下,在他们的创业过程中,传统的军事及其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,他们军事方面的优势或长项也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,尤其随着征伐目标的改变发生了变化。而这些变化则更多地体现在了水军的训练和军事科技的应用,以及军事匠人的培养上。因此,本文仅就元代的水军训练和军事科技教育问题进行一番探讨,错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。
一
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以后,随着征伐南宋步伐的加快,他在军事方面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那就是蒙古铁骑到了长江流域或江南水乡以后,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——其优势的发挥遇到了困难。从一定意义上讲,在渡江战役中,由于南宋水军的顽强抵抗,蒙古军的优势变成了劣势。为了适应新的形势,尤其要适应长江流域及江南水乡的地形特点,必须尽快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军。只有这样,才能掌握主动权,从胜利走向胜利,进而实现收复江南的任务,完成统一大业。相反,若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,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将成为泡影。可见,组建水军意义重大,迫在眉睫,必须抓紧落实。因此,元代的水军是在讨伐的战争实践中诞生的。据史料记载,元代的水军最早在元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,于1238年开始组建。当时水军的组建,与易州(今河北易县)定兴(今河北保定)人解诚有这密切的关系。此人“善水战,从伐宋,设方略,夺敌船千计,以功授金符、水军万户,兼都水监使。焦湖之战,获战舰三百艘。宋以舟师来援,诚据舟厉声呵之,援兵不敢动,急移舟抵岸,乘势追杀之,夺其军饷三百余斛……从攻鄂(今湖北武昌),夺敌舰千余艘”。这里所说的焦湖之战,是指戊戌年(1238年)在今天的安徽巢湖蒙宋双方进行的一次激战。这些史实都说明,大蒙古国时期的水军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,而且水军都督基本上都有汉人来充任。后来1258年元宪宗蒙哥率军征南宋时,曾经“募兵习水战”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任务就是朱国宝“以职官子从军,隶水军万户解诚麾下”。以上就是元代有关水军的最早记录,为此解诚为创建大蒙古国以及元代的水军立下了汗马功劳,同时也为水军的训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水军的创建标志着蒙古族军事教育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,也为推翻南宋王朝奠定了强大的水军基础。
仅仅创建了水军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提高它的作战能力,而且必须敢打硬仗。因此,元朝政府开始结合实战加强了水军的训练,也积累了好多成功的经验。据史料记载,至元二年(1265年)三月,政府下令“敕边军习水战”。这一敕令看似简单,但意义深远。此时忽必烈的目光早已锁定南宋的广大地区,而且在征战时绝对不能重蹈赤壁(今湖北赤壁,还有一种说法为今湖北嘉鱼或黄州)大战的覆辙。当年曹操在赤壁失利的原因很多,但其中的一点是北方人不习水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。所以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忽必烈早已看到了这一点,而且做了具体的部署。这也是元朝政府训练水军的最早记录。由于记录过于简略,具体在哪几个方面进行重点训练,其教官是谁等问题都成了一个未知数。至元四年(1267年)东安(今河北安次,即廊坊)人张禧“改水军总管,益其军二千五百,令习水战”,与之相适应,他的军功基本上都与水战和海战有着密切的联系,而且大多是在均州(今湖北均县即丹江口)、襄樊(今湖北襄樊)、襄阳(今湖北襄阳)、江阴(今江苏江阴)、日本等地的水域和海面开战的。总之,元朝政府通过军事斗争进一步强化了水军的训练,初步达到了克敌制胜的目的。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。元朝政府在加强水军训练的同时,对船只或战舰的生产给予了高度重视,也做了很多实事。至元五年(1268年)正月,元朝政府下令“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”。训练水军没有舰船是不行的,假如没有舰船,那所有的东西都将成为一句空话。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去制造战舰。至元六年(1269年)七月,兀良氏阿朮将军在汉水与宋军交战,杀溺生擒五千余人,获战船百余艘;于是治战船,教水军。这是边战边学,非常实用提高也快。在平宋战场上阿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他最具有发言权。至元七年(1270年)三月,阿朮与刘整言:“围襄阳,必当以教水军,造战舰为先务”;这一建议得到朝廷的许可之后,他们教水军七万余人,造战舰五千艘。阿朮和刘整通过敌我双方实力的比较后,他们可谓知己知彼,一方面看到了宋军的长处,另一方面也深深地体验到了自己的短处。“我精兵突骑,所当者破,唯水战不如宋耳。夺彼所长,造战舰,习水军,则事济矣”。这就是前线将士破宋的基本思路,也算是一个具体的作战方案。然而,真正要教练水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事情,他需要很长的时间。至元十年(1273年)三月,刘整提出的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(今陕西汉中或南郑)金(今陕西金水)、洋州(今陕西洋县)、汴梁(今河南开封)等处造船二千艘的请求,得到了元廷的批准。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强元朝水军的实力,从而加速了南宋灭亡的进程。这一点,我们可以从元代的“曹彬”——伯颜的“剑指青山山欲裂,马饮长江江欲竭。精兵百万下江南,干戈不染生灵血”诗文得以了解。这篇诗文气势磅礴,寥寥数语展现了作者非凡的气度,同时也为我们描述了蒙古铁骑和水军的声威。对此元人刘敏中的记录更有意思:“丞相总兵南伐,旗旄所向,战无坚阵,望风披靡,长驱径捣,如入无人之境;取汉鄂如拾遗,摧苏杭如拉朽,宋将身窜胆落,救死之不暇,用能获其君臣,收全功而还”。笔者通读《平宋录》后的感觉是,元军一方面用武力解决问题,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利用政治手段解决了好多棘手的问题,这样免去了生灵涂炭,为百姓谋取了福祉。伯颜的高明在于彻头彻尾地贯彻了元世祖忽必烈制定的“不杀”之策。
元朝统治者在征南宋同时,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这一岛国。海上作战为元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此时蒙古军把自己的长项搁置一边,勇敢地学起了原来自己不懂的东西。海上作战首先必须熟悉内河作战,后者是前者的基础。内河作战熟练到一定程度之后,至元十一年(1274年)三月,元廷“命凤州(今陕西凤县)经略使忻都、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,以千料舟、拔都鲁轻疾舟、汲水小舟个三百,共九百艘,载士卒一万五千,期以七月征日本”。这次征日本虽然失败,但积累了海上作战的经验。为了更好地组织下一次的海战,元廷进一步加大了水军训练的力度。至元十六年(1279年)十一月,政府“命湖北道宣慰使刘深教练鄂州、汉阳(今湖北汉阳)新附军”。至元十八年(1281年),政府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、右丞范文虎及忻都、洪茶丘等率十万人征日本;八月以阿塔海代总军事征日本,因遇台风而失败。当时人们对海上的气候还是缺乏了解,再加上天不作美导致了失败。假如元军能够错开台风,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写法了。为此,日本人至今称神风帮助他们打败元军(寇)。至元二十年(1283年)正月,政府命右丞阇里帖木儿及万户三十五人、蒙古军习舟师者二千人、探马赤万人、习水战者五百人征日本。由于各种原因,此次未能成行。此后,水军的训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。至元二十二年(1285年)二月,元廷以军万人隶江浙行省习水战。同年四月,以征日本船运粮江淮及教军水战。同年十二月,江淮行省以战船千艘习水战江中。至元二十三年(1286年)十月,元廷“谕江南各省所统军官教练水军”。至元二十四年(1287年),塔不已儿之子庆孙领诸翼军镇太湖,教习水战。至元二十五年(1288年)六月,“诏蒙古人总汉军,阅习水战”。到了这个时候,在蒙古人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熟悉水战的将领。实际上,元廷加强水军训练的目的非常明确,那就是不甘心远征日本的失败,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南海列岛。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二月,元廷诏福建行省除史弼、亦黑迷失、高兴平章政事,征爪哇(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);会福建、江西、湖广三行省兵二万,发舟千艘,给粮一年,驶向了爪哇。据载,本次海上远征,元军历经千难万险,取得了一定的战绩,但由于势单力孤,花了了六十八昼夜时间才回到了泉州,伤亡三千余人。这是元军东征日本失败后的第一次胜利。成宗即位以后,于至元三十一年(1294年)九月,以合鲁剌及乃颜之党七百余人隶同知枢密院事不怜吉带,习水战。大德六年(1302年)正月,海道漕运船,令探马赤军与江南水手相参教习,以防海盗。仁宗即位后,也不同程度地加强了水军训练。皇庆元年(1312年)四月,命浙东都元帅郑祐同江浙军官教练水军。到了这个时候,随着战事的减少,史书上有关水军训练的记载日趋减少,或者说见不到了。元朝统治者在较短的时间里,组建并训练出了强大的的水军,而且主动出击日本和爪哇,这在中国历史上奏响了一曲曲骑士的凯歌。与明代的抗倭斗争相比,元代的东征日本绝对是一个英雄的壮举。前者是在家门口受凌辱,窝囊到了极点,而后者却打到了日本列岛,虽败犹荣。
二
除了水军的训练,元代蒙古统治者对军事科技及其教育也给予了高度重视:
首先,蒙古军在南征北伐时,开始使用了指南针。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,而且蒙古人通过战争把它传到了西方。按理说,蒙古人的方位知觉还是比较灵敏的,但在某些场合还辅助于先进的仪器设备,尤其在空旷的原野或茂密的森林里还必须有指南针。到目前为止,笔者还未见到有关蒙古人使用指南针的记载,如果据此做出否定的结论,那就错了。在此我们可以把陆地作战抛在一边不管,而海上远征就不同于陆地作战了。元军东征日本,南征爪哇,海上的风浪大,暗礁又多,假如没有指南针,那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。当时的远航,一方面要用指南针,另一方面还需要定位仪,用来确定战舰的具体位置。若没有类似的仪器设备,偏离航线、触礁沉船的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航海技术所达到的那个水准,以及船员的素质。指南针或定位仪的使用,以及舵手的培养都需要有相应的教育。那么,首次向蒙古人传授上述技术的人又是谁呢?是不是汉人呢?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探讨。在一般情况下,蒙古人比较重视匠人,这些匠人的言传身教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
据史料记载,在元代的军事教育中,人们已经广泛运用了军用地图。在当时一个高级指挥官必须善于利用军用地图,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。这方面元世祖忽必烈在指挥作战时,特别重视看地图。据史料记载,忽必烈“尝坐便殿,阅江南、海东舆地图,欲召知者询其险易”。由此可见,军事指挥员查看地图,用以部署兵力都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。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当时编写方志中可以了解,其中所附的山川河流图很能说明问题。因此当时的军用地图可能更详细一些,甚至把每一个战役中的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,标注的清清楚楚。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者,身边必须有一张地图。另外,当时的海战已经开始运用了海况图。至元十八年(1281年)三月,由日本船为风漂至者,令其水工画地图,因见近太宰府西有平户岛者,周围皆水,可屯军船;决定先占据这一岛屿,再由一岐岛进讨日本。据此推理,元军在征爪哇时也可能画过海图,为认识海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。
其次,充分利用砲石技术,培养了一批砲手。与大蒙古国时期相比,元代的砲石技术及其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,砲兵成了一个特殊的兵种。在元代的军队管理机构中,有砲兵手千户所,而且安排了多名官员。换句话说,当时砲手的培养,主要由砲兵手千户所来管理。除此之外,元朝政府还设置了“回回砲手军匠上万户府,秩正三品。至元十一年(1274年),置砲手总管府。十八年(1281年),始立为都元帅府。二十二年(1285年),改为万户府”,并设置了多名官员。该机构主要管理回回砲的制造以及砲手的培养等工作,因此它既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,也是一个业务培训机构。回回砲的传入是中西方科技交流的产物,蒙古人西征把回回砲带到了中国。
在成吉思汗时期,除了唵木海,还有砲手贾塔剌浑和砲手元帅薛塔剌海,他们都兼任过砲手教官,为攻城掠地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到了忽必烈时期,贾塔剌浑的弟六十八立砲樊城南、发砲摧常州城壁、总新附砲手军、管领砲手都元帅、更授砲手军匠万户,尤其在训练砲手方面功不可没。毫无疑问,这些人也向蒙古军传递过砲石技术。
除此之外,蒙古人在攻城掠地时,已经广泛地使用回回砲了。当事回回砲匠们的技术精湛,准确率高。当年旭烈兀的军队进攻篾牙法里勤(其地应该在伊利汗国境内,但具体位置不清楚)时,敌我双方进行了砲战,而且射出去的砲石在空中撞击,碎裂成小块,砲匠们的高超技艺让人惊叹不已。在元朝较早传授回回砲石技术的人很可能就是亦思马因。至元九年(1272年)十一月,“回回亦思马因创作巨石砲来献,用力省而所击甚远,命送襄阳军前用之”。除了亦思马因,阿老瓦丁在制作回回砲方面也很有名。他于至元八年(1271年)同亦思马因一起来元廷的。这两位都是回回砲石技术的传承人。据史料记载,至元十年(1273年)亦思马因“从国兵攻襄阳未下,(他)相地势,置砲于城东南隅,重一百五十斤,机发,声震天地,所击无不摧陷,入地七尺。宋安抚吕文焕惧,以城降”,因此他后来荣升为回回砲手总管。对于这一点,在阿里海牙传里也有所提及。另外,马可波罗也做了相应的记载:“尼克罗和马飞两兄弟……制造一种西方人用的机器。这种机器能投射重达一百一十二公斤的石头。如果使用这种机器,可以毁掉这座城市的建筑物,砸死居民。大汗大喜并准奏。他召来最优秀的铁匠和木匠,听从者两个兄弟的指挥……几天之内工匠们依照波罗兄弟的指示造出了他们的军用投石机,并且在大汗和整个朝臣面前进行试用,使他们有机会看到这种机器抛射石头的情景……当这种机器在襄阳府前架好后,其中一台机器先射出第一块石头,达到建筑物上,又猛烈又沉重,致使这座建筑物大部分塌倒在地,居民们被这种奇怪武器,吓得惊恐万状,他们似乎以为这是天雷在起作用,所以马上投降”。这些记载虽说有点出入,但大体相同。后来冯家升先生对回回砲的图纸进行了复原,冯立升先生对回回砲也进行了深入研究,所有这些为我们了解回回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。
平宋以后,元朝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回回砲匠及砲手的培养。至元十六年(1279年)三月,囊加带括两淮造回回砲新附军匠六百,及蒙古、回回、汉人新附人能造砲者,俱至京师。至元十八年(1281年)七月,括回回手散居他郡者,悉令赴南京屯田。至元二十年(1283年)四月,发大都所造回回砲及其匠张林等,付东征行省进行了训练。至元二十一年(1284年)改砲手元帅府为万户府,砲手都元帅府为回回砲手军匠万户府。这些改革,都有利于砲匠和砲手的培养。在战事日趋减少的情况下,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,感觉很有意义。至治三年(1323年)正月,遣回回砲手万户赴汝宁(今河南汝南)、新菜(今河南新菜),遵世祖旧制,教习砲法。在当时砲匠的子孙后代是世袭的,因而其技艺的传承,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。
元代人们在用砲石的同时,也开始使用了一些火炮。另据史料记载,“蒙古人有能祈雨者,辄以石子数枚,浸于水盆中玩弄,口念咒语,多获应验。石子名曰鮓答,乃走兽腹中之石。大者如鸡子,小者不一,但得牛马者为贵,恐亦是牛黄狗宝之类”。鮓答即札答()不仅在《蒙古秘史》中出现过,对此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也做了相应的记载。后来,拖雷在征潼关(今陕西潼关)的时命令手下人施用过类似的法术。应该说,到了元代蒙古人将这些法术也进行了传承,用以嚇退敌人。
  
(宋)曾公亮《武经总要前集》卷十二《守城并器具图附》,见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第3册,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,第604、617、620页
 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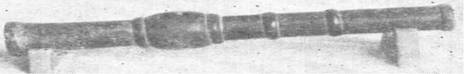
见冯家升著《火药的发明和西传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,第52、37、38页
|


